博览与庭训
冯天瑜成长于辛亥首义之城武昌,他的父亲冯永轩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名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一期生,受教于梁启超和王国维,专攻历史考据学。冯永轩1926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时,梁启超集宋词名句、王国维选取东晋陶渊明《饮酒诗》之一,手书赠予他。梁、王条幅长年悬挂于冯家堂屋,冯永轩又时常谈及二位先生道德文章及种种逸事,故冯天瑜自幼就对梁、王二公有一种家中长老的亲切感。
冯天瑜自幼酷爱文史,自少年时代便泛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史地书籍。这首先得惠于他就职湖北省图书馆的母亲张秀宜。冯天瑜自小学3年级至高中毕业,一直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每天放学归来,照例到母亲主管的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初中以后,为图书馆浩博的藏书所吸引,遂改弦易辙,变为成人阅览室的常客。令他摇情动魄、形诸舞咏的首推中外文学名著。早年从这些名著中获得的对于中西文化的感悟,大有益于他后来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尤其有助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展开。

少时冯天瑜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这类书的阅读经验,使得他足不出户,便可神交古人,泛游九州。有段时间,他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常一连几小时阅看不息,以至于可以随手绘出中国各省区及世界各国的版图轮廓。这种生动而具体的空间感的培育,对于冯天瑜日后成为史家,也有特别意义。因为历史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之内运行,史家必须同时具备清晰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意识,才能真切把握人物、事件的质地感、度量感,如历其境地体察古事古人。如此“左图右史”“知人论世”,方能达到对研究对象同情的理解。
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幼年以来的积累,冯天瑜子承父业进大学历史系本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高中毕业前,家庭的变故断绝了他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冯天瑜只得报考与政治背景不相干的生物系,成了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的一名学生,但他对于文史的热爱却始终没有消退。
大学期间,冯天瑜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陆续发表了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杂文。冯永轩对于儿子喜爱文史甚感欣慰,便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连续几个寒暑假,给他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他由泛泛阅览到逐渐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步入研习经典的大门,正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的这段庭训。
历史文化语义学
1994年,冯天瑜调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站在珞珈山上,学术视野更为辽阔,除了中华文化史、明清文化转型研究以外,他还开辟了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等全新研究领域。自1998年起,他有近五年时间在日本授课并从事研究,得与多国汉学家论难究学,并潜心开掘异域史料,进行中、西、日文化比较,将文化转型研究向深广处拓展。
1998年至2001年,应日本爱知大学之聘,冯天瑜在该校现代中国学部担任专任教授,讲授有关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课程。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他得以切身体验日本社会,并利用日本丰富而便捷的藏书系统,从容思考中日文化比较和中日文化交互关系诸问题。冯天瑜选定“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作为研究方向,这既是探索中日关系的富于特色的角度,又能借助日本人周密、系统的实证考察,为近代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和参照系。
他以“幕末日本第一次访清使团”为具体的研究课题,并在方法论上应用陈寅恪概括王国维“二重证据”的三条做法之两条——“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写成《“千岁丸”上海行》一书,“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茅家琦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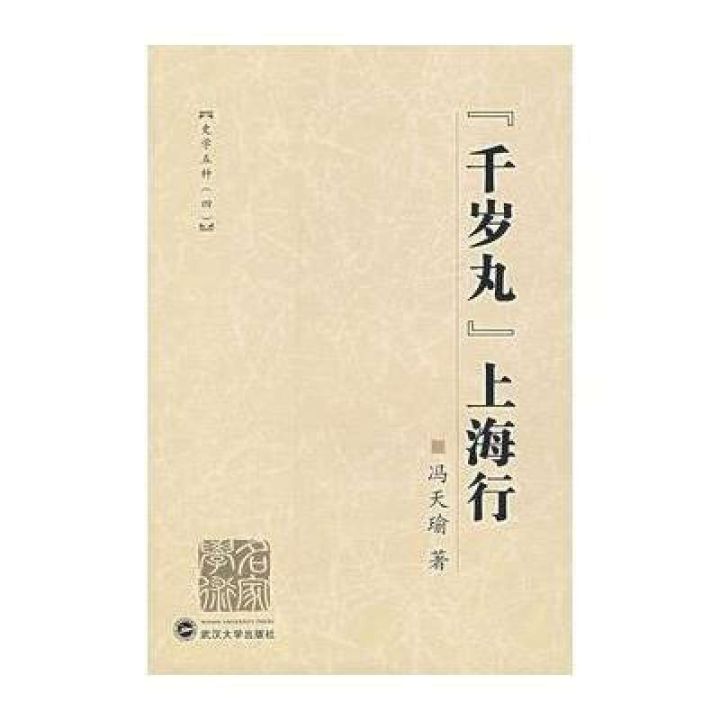
考究术语生成史,是冯天瑜在日本讲学期间的另一致思领域。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本是冯天瑜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便设立专题,详加考释,通过对“几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学”“文化”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别是清朝民国之际中、西、日文化交会间的思想因革状态。
但直到讲学日本期间,他才自觉地将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正式作为一个文化史研究课题。他于此提出“历史文化语义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转换、东西交会的时空坐标上展开研究,不仅对诸多汉字新语的生成、演变寻流讨源,而且透过语义的窗口,观照语义变迁中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展现中国近代异彩纷呈、后浪逐前浪的历史文化状貌。
特别是2004年到2005年间,冯天瑜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担任“外国人研究员”,主持多国学者参加的“东亚诸概念之成立”项目研究,得以将思索多年的课题“封建辨析”徐徐展开,写成《“封建”考论》之大著。

《“封建”考论》问世后,学界反响热烈,引发海内外之讨论热潮,至今未息。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认为,冯天瑜对“封建”作了前所未有的考辨,极具学术价值。《“封建”考论》被誉为“精湛的‘封建’概念学术史”(方维规语),是“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的大制作(张绪山语),堪称封建社会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根蟠语)。学界的讨论辑有两本评论集:《“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中国文化生成史
近年来,冯天瑜集合、凝练、提升30多年来关于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国当下的生存实态为窥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议题,考析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及中外文化交互关系,于2014年再次出版皇皇八十万言的《中国文化生成史》,这是他继《中华文化史》之后的又一文化史整体通论著作,可说是冯天瑜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不满足于对个别“文化英雄”天纵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于对某些引发剧变的短暂历史事变的关心,而是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对中国文化的生成作“长时段”辨析,着眼考察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合成的“结构”对文化的推动及制约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层动力机制”,以达到对中国文化的全景式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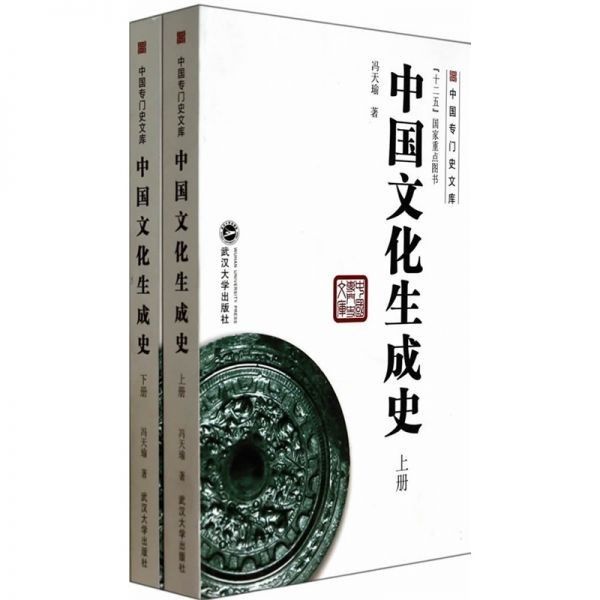
《中国文化生成史》既是中国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作了前瞻性探讨。它并未停留在对既成中国文化的历史解释,而是以当下为分界点,着眼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作理论前瞻。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在人们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能获得其历史性。社会现实构成了历史反思的起点。
《中国文化生成史》在详尽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生成机制的基础上,不忘观照当下,对中国复兴、文化创新、文明对话等热点问题多有评议。
冯天瑜自谦为学术界一施工匠人,但言及勤勉则不遑多让。2004年到2005年间,他在日本文部科学省设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多国学者参加的“东亚诸概念之成立”项目研究。
据日本工作人员说,自日文研成立之日起,未见勤奋如冯先生者。2005年8月他归国之时,日文研工作人员特地起早赶来,列队相送,以示敬意。熟悉他的人常说,他的学术与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迄今他虽年逾古稀,仍心织笔耕,意趣高昂,哪怕是近来患重疾住院,仍手不释卷。他在生病期间撰写的五十余万言的《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于今年7月刊行。于他而言,学术就是生活,学术就是生命。
冯天瑜治史,一贯奉行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力求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他说:“精思义理,苦心考据,擅长词(辞)章,并致力于三者间的‘相济’,于弘大处着眼,从精微处着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良史。”(《回眸学术理路》)
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辞章是形诸笔端落实于纸上的最后程序,义理、考据能否实现,端赖如何书写。在辞章方面,冯天瑜主张述事纪实,务求清顺流畅,娓娓道来;辩驳说理,则讲究逻辑层次,条分缕析;无论哪类文字,都切忌板起脸孔,而应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寓庄于谐。邱汉生称赞冯著“语言生动,使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论证更具有引人入胜的力量”。

众所周知,冯天瑜文笔甚佳,既能写细密严谨的学术著作,也能写娓娓道来的学术散文,是当代为数不多的文史兼通的大家。对于当下史学界在专业的旗号下,忽略文章的辞章美感和可读性,冯氏论著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谢远笋,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概念史视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台湾思想文化史及现代新儒学研究。
文化学与中国文化史学
冯天瑜自幼博览,所获非止童趣,亦为人文启蒙,更养成喜读之性,“文革”期间亦不曾中断。20世纪70年代后期,冯天瑜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经再三权衡,他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跨入史学之门,自1979年开始,任教于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今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由于目睹近三十年史学研究偏重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文化史久遭冷落,自己又对文史哲均有涉猎,且稍长于综合,冯天瑜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作为专攻——此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之前四五年。

当时,冯天瑜已进中年,且非史学专业出身,但不数载,便以《明清文化史散论》(1984)享誉学界,这确乎令人称奇。此书作为冯氏的首部文化史专著,即被认为是“超过前人”之作,“已足以与柳先生(即柳诒徵)方轨”。(邱汉生语)其实,就其个人历程说来,这一切诚可谓蓄之久远,发于天然——他自幼即尽日徜徉书林,陶成人文之质,且有当代学人少有的家学渊源。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为了打破传统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的困局,梁任公提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新史学。在摒弃传统王朝政治史转而书写人群进化现象的新史学革命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发其端绪。梁氏在《中国史叙论》中,表示有心撰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化通史,可惜天不假年,其生前面世的只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国文化史目录》等少数篇目。
1914年,林传甲所著的《中国文化史》面世,大约可算作目前所见的最早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著作了。此后,随着中国文化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第一次热潮,出版了众多以中国文化史为名的经典之作,如柳诒徵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193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钱穆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由梁启超开启,经柳诒徵等人发展的文化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归于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断了30余年之后方重新兴起,至今在诸多领域方兴未艾。冯天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便自觉接续这一学术传统,冯著《中华文化史》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史整体与系统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他常自谦说自己不过是追随前辈、时贤的一施工匠人,但他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与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早已是学界共识。冯氏在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研究领域的创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文化生态”说。冯天瑜遵循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学基本论题,如中国文化之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尝试以“文化生态”说为基旨,阐述文化学理论,建立中国文化史框架。主要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上篇(1990),还有《中国文化史断想》(1989)《人文论衡》(1997)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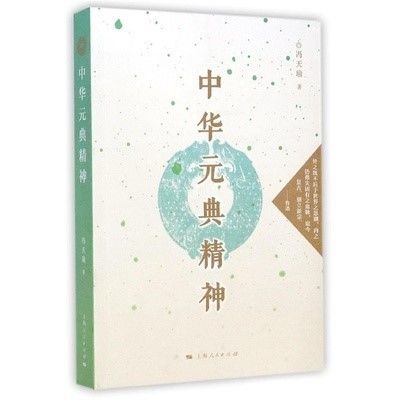
其二是“元典精神”说。冯天瑜追踪中国文化演绎史,注重“生成”与“转型”两环节,聚焦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为中华文化生成之“轴心时代”,此间形成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之文化经典,他拟名为“元典”,探索中华元典形成过程、内在结构及其常释常新之诠释史。“晚清”为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期,在晚清文化研究中,力辟直线进化观和西方中心论,考究发生于明清间以“复归元典”为外显形态、以螺旋上升为运动方式的“文化重演律”。此类探幽阐微之考析,集结于《中华元典精神》(1994)。

冯天瑜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张岱年语),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也由此奠定了此类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其间,冯天瑜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张之洞评传》(1994)、《辛亥首义史》(2011)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后一研究中,广采乡邦文献,详考切关宏旨的首义史事细节,又适度使用访录辛亥老人的材料,堪为“口述史学”之典范。冯天瑜长期担任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纂,主持湖北省、武汉市的地方志修纂。文化史与地方史构成冯天瑜治史之一体两翼。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45号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45号 联系电话:027-87839901 027-87324788
联系电话:027-87839901 027-87324788 传真:027-87250783 邮编:430070
传真:027-87250783 邮编:430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