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陈才俊,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
东西方文化对话与中华文化的抉择(上)
文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有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否定的、消极的另一面。文化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与不同社会的接触而受到影响,可能会催促自身的演变,也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阻止自身的演变。然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文化所承载的使命一直在追求和促进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一、人类文明的衍演与文化体系的构筑
陈才俊:章先生,您好!我们曾经就“人类文明建构”这一主题进行过讨论,但谈得更多的是对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人文精神缺失、价值体系沦丧的担忧,以及对人类文明重建的一些构想。其实,人类文明构成的核心要件——文化问题本身,才是人类文明重构之关键所在,值得深入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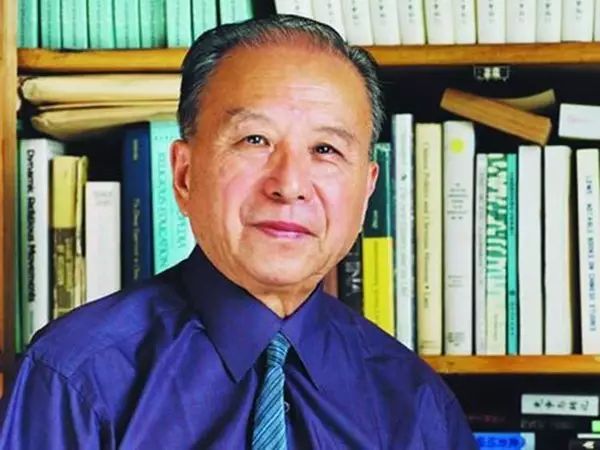
章开沅先生
章开沅:是的。按照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解释,人类文明的初始形态大致有二:一是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经济文化的地区,如黄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一是指文化类似的人群,如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宗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显而易见,文明的内核是文化。可以说,文化的生成、演变、传播、交汇与融合,对人类文明的产生、衍演、完善与流变,厥功至伟。
陈才俊:“文化”一词的出现及其在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中的衍演,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自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前43年)首次以拉丁文“cultura animi”表述“文化”概念以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视阈出发,通过解析世界不同的文明体系来探究文化的意涵,虽然至今仍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但有一点共识则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文化是人类文明构成的主体。文化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其代表作Primitive Culture(《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此被视为对文化比较经典的阐释,亦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
章开沅:不过,文化和文明还是有内在区别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相较而言,文化偏于“内”,注重精神层面,其本质是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总是要通过特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文明则偏于“外”,是上述特定文化形态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所呈现出的总体的和基本的价值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是不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关于人对自己、人与世界所达到的基本价值程度的发展标志。
由于人类精神活动或思维联系的指向千差万别,所以,文化呈现出政治、经济、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形态。而相近的文化形态,又可分为偏重于物质和偏重于精神两大体系。于是,人们就把偏重于物质形态的文化,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等称为物质文化形态,把其中所包含的物质文化的价值尺度称为物质文明;把某种思想制度、行为规范、精神成果(包括哲学、宗教、文学等)称为精神文化形态,把其中所蕴涵的人类精神文化的价值尺度称为精神文明。邓小平曾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以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并将其确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他的这一提法显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陈才俊:从对文化与文明的比较,似乎可以看出文化的两大显性特征。其一,既然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那么人思维活动的活跃性和意识活动的不间断性,则决定了文化的动态性特征。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形态都是活动的有机体,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比如当我们研究某一古代文化形态时,绝对不可囿于一个固定不变的僵死概念或者某种没有生命的知识范畴,而是应该通过深掘各种历史遗迹、历史资料乃至历史现象,来把握该古代文化形态所反映的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联系的运动过程,揭示其时各种政治、经济、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所包含和体现的人类思维特征以及认识能力所达到的程度。另外,由于动态的文化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所以文化总是发生着变化。于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形态常常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风貌,体现着不同的内涵构成。
其二,鉴于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所以又具有鲜明的差异性特征。因时代、地域、族群乃至自然环境的不同,文化不仅表现出发展程度的差别,而且呈现出禀性气质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禀性气质差异中,还存在不同文化体系内涵的差别和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异。所以,文化不仅有古代与现代之分,而且有东方与西方之别;不仅有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之异,更有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差。也正是因为文化所具备的差异性特征,才导致人类不同文化形态的百花齐放与争妍斗艳。
章开沅:通过阐释文化的动态性和差异性特征,我们还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深层关系。一方面,文化与文明有着各自不同的本质特性。文化是动态的发展过程,文明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文化价值总体。另一方面,文化是文明的内核,文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存在。文明作为文化的价值总体和较为恒定的价值内涵,必然蕴藏于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态之中。同时,也正是各种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彰显着文明的价值体系。
陈才俊:人类文明的产生、衍演、完善与流变,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早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已实现第一次分工,产生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不易形成大规模的聚居场所,故对文字没有迫切需要。而农耕民族则不同,不仅有固定的居所,而且有固定的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农耕民族这种生活方式既容易形成大的部落,亦为“早期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土壤。一般认为,文字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之一。文字符号的出现,促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人类第二次分工,为“中期文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石。文字的定型,更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文字是人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明。人类的个体能够通过文字记录的信息,获得人类整体在漫长岁月里创造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字使人类的思维更加缜密,使文明的传承得到保障。
章开沅:一般而言,界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几个重要标准是:青铜器的大量使用、文字的大规模运用、城市的诞生,以及大型宗教礼仪设施的出现。世界几大重要古代文明体系的问世,均符合上述标准。
不过,与其他文明体系相较,古代中华文明则呈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中华文明有三个直接源头: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它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农耕民族为主体。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并与渗入,黄河、长江流域以古代华夏族群为主体的汉民族体系不断融入北方民族元素。同时,包括西域族群在内的外来民族渐趋被汉民族所吸纳与同化。而且,古代汉文化亦多次融释周边其他民族文化与西域文化。所以,中华文明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与“蛮、夷、戎、狄”各区域、各民族古代文明长期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不断融合的文化结晶。
陈才俊:如前所述,文化具有差异性特征,不同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由于宗教信仰、族群认同、政治主张、价值理念等不同,或者教育程度、语言体系、文学修养、艺术旨归等有异,人类文明在演进过程中诞生过许多不同的文化体系。数千年之后,有的文化因为各种原因而消失了,有的文化则在竞争乃至扩张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载体。
章开沅: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有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否定的、消极的另一面。文化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与不同社会的接触而受到影响,可能会催促自身的演变,也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阻止自身的演变。然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文化所承载的使命一直在追求和促进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二、宗教文化的勃兴与多元文化的繁盛
陈才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曾经指出,任何一种文明发展的轨迹均取决于该文明精神水平的进步或衰退,文明的过程本质上是精神的提升与衰退,而精神提升与衰退的载体和根据则是宗教。他还把宗教喻为一辆四轮马车,认为文明就是宗教运行的车轮,正是通过文明单调重复的周期性循环,形成了宗教朝着既定方向、具有更长节奏的运动。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宗教的性质决定着文明的性质,宗教的兴衰决定着文明的兴衰;宗教乃是“文明的核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其产生和兴盛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
章开沅: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的宗教发展历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发展历史。在人类社会早期,宗教创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宗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各种文化无不从宗教吸取有用的养分,并通过宗教活动来展现自己的存在,继之获得自己的表现形式。人类先后创造的三大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影响过、正在影响而且一定仍将继续影响世界文明的诸多方面。人类历史上的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均深受各种宗教的影响。
陈才俊:文化之为文化,最根本之意在于“化”。化者,变也,改变或者变化之谓。文化有三个基本要义:首先是“化”,其次是“人化”,再次是“化人”。由于文化的第一要义乃“化”,其终极旨归是化“人”,故“化人”乃文化的中心义和至上义。如果我们探究宗教的文化属性与文化功能,不难发现,其本质属性与功能正是“化人”。
文化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形成一个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体系。而宗教正是一种由“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组合而成的文化体系。首先,不仅宗教建筑,如佛教的寺院、基督宗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道教的宫观等,属于宗教的器物层面,而且佛教的袈裟、基督宗教的十字架和麦加克尔白的黑石、道教的道袍等,也都属于宗教的器物层面。其次,作为宗教要素的宗教制度或宗教体制,如佛教的寺院制或基督宗教的主教制、公理制和牧首制等,均为宗教的制度层面。最后,姑且不论宗教神学均有观念系统,仅就宗教信仰对象而言,亦无一不是某种精神存在,如佛教的佛陀、犹太教的耶和华 、基督宗教的上帝和耶稣基督、伊斯兰教的安拉、道教的三清尊神等,均是精神性的存在。
章开沅:宗教是人类最早的、全覆盖的、系统性的文化形态,严格来讲,更多属于关涉人生意义和终极目标的精神文化层面。宗教为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如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语言文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民俗风情、文化交流等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智慧、精神营养和实践经验。比如,其关于宇宙生成和人类起源的原始神话以及各种富于幻想的美丽传说,催发哲学和文学的萌芽;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信条和禁忌,成为伦理和道德的初级形态。宗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构成了人类文明衍演的主线。
宗教居于民族文化的核心地位,是大多数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的精神内核,维系着民族共同体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的延续。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虽然曾建立过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而且声震遐迩,显赫一时,最终却土崩瓦解,坍塌解体。究其原因,乃其没有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至高无上的宗教。而犹太民族,因一直秉持共同的民族信仰——犹太教,故虽然颠沛流离,饱经沧桑,但其文明却经受住几千年极其严峻的考验,且至今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陈才俊:宗教对整个文化模式的建构与转型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宗教对人的生命活动也具有内在与外在的双重规范功能,既给人的生命活动以勇气和力量,亦通过禁忌、戒律对人的欲望和激情予以束缚。宗教的这种双重规范功能,广泛地渗透于民族及社会的伦理道德与社会风尚之中,一方面促进文化形态的转型,另一方面又对文化形态的稳定起到巩固作用。宗教在文化体系中为人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和勇气源泉,提供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对文化体系的确立和变革提供调控,使人的生存有所遵循。
章开沅:所以,宗教的发展与繁盛,有利于人类创造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异质文化。印度文化、“犹太-基督宗教”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便是宗教色彩非常浓郁的几大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早已被宗教学家所证明。构成中华文化基石的儒、道、墨诸家,均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更遑论佛教的渗入。另外,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以宗教为主要精神依托,有些民族甚至全民信教。
另外,人类社会文化的演进,乃是由宗教文化与人本文化交汇融通、相互砥砺、彼此吸纳而共同推动的。比如,中华文化以儒、释、道互为发展主轴,其中,儒为人本学说而带有宗教性,释为佛教哲学与佛教宗教,道为宗教哲学与道教神学。再如,欧美文化以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互动为发展主脉,其中,希伯来文化为宗教文化,希腊文化为人本文化。
陈才俊:世界几大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随着宗教的繁盛而呈动态发展模式。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希腊文化起初都是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散到周边。中华文化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印度文化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希伯来-希腊文化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中国和印度的新兴文明通常仍然由起初的文明核心区域主导支配,而西方则不同,罗马凭借军事上的优势,不仅征服希腊本土,还征服了中东的西部地区。这几大文化体系的衍演与扩展,均是以宗教作为内在驱动力量。
章开沅:由于思维方式不同,东西方文化秉性存在本质差异。从现象上看,中华文化是“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是“法理型”文化。中华文化弘扬“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主张建立良好的伦理道德以规范人的行为;强调通过教化来使人形成自律意识,自觉克服人的动物性本能,克服个人私欲,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西方文化则侧重“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主张“原罪说”;强调人生下来就有罪,主张通过严密的法律抑制个人的私欲和动物性本能,以“他律”来促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
文化倾向的不同,导致东西方民族在宗教信仰上出现很大的差异性。其具体表现是,中国人兼容,西方人专一;中国人重功利回报,西方人重精神寄托。从信仰形式来看,中国人不排他,许多人既信仰佛教,也信仰道教或其他宗教;西方人不仅只信仰一种宗教,不会既信仰基督宗教又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只信仰一神教。从信仰目的来看,中国人功利心很强,祈求目的很明确,重恩赐和回报;而西方人则目的性不强,重忏悔和宽恕。正如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所言:“我们从犹太人那里学到了不宽容的看法,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接受别的宗教。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都有这样正统的教义,规定没有人可同时信仰这两个宗教。而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不相容;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同时又是孔教徒,两者并行而不悖。”

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罗素
陈才俊: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关注的根本是生命、生活和生死的问题。因为价值理念的不同,决定了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几大世界文化体系。印度文化、“犹太-基督宗教”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现世”(This World)均持消极或否定的态度,认为“现世”是虚幻的或在整体上堕落、有罪;认为生命本身永不终结,终结的只是肉体。因此,它们认为,生命的终极归宿在“现世”之外而不是之中,必须通过宗教修炼的手段来彻底摆脱“现世”。而中华文化很早就表现出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现世”——即“天地”或“六合”——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形成以此岸为取向的高度世俗化文化;相反,对于“现世”之外的世界,即“天地”之外有无“天地”、“六合”之外有无“六合”,基本持否定或存而不论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肉体死后的生命采取消极怀疑的态度。从根子上讲,中国人相信世界只有一个,即以“天地”为框架、以“六合”为范围的“现世”。中华文化的这一特点,导致中国人非常重视天下的“和合”或者“和谐”。
章开沅: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均发端于宗教,实际上是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中华文化与基督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精神生活的支柱与中华文化的基石。基督宗教文化背后,屹立着源远流长的希伯来-希腊文化发展至今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华文化与基督宗教文化的交融,远远没有取得像与佛教文化那样水乳交融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使之中国化,还远远没有形成。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主体文化不可能被佛教文化或基督宗教文化同化,但也不可能把佛教和基督宗教排斥于国门之外。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成为历史的必然,无法阻挡。
原载《澳门研究》2016年第2期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45号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东路45号 联系电话:027-87839901 027-87324788
联系电话:027-87839901 027-87324788 传真:027-87250783 邮编:430070
传真:027-87250783 邮编:430070



